男女主角分别是杨一木林芳的女频言情小说《重生1981:开局坟头挖宝!:杨一木林芳番外笔趣阁》,由网络作家“末名客”所著,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,本站纯净无弹窗,精彩内容欢迎阅读!小说详情介绍:杨一木又直接点明了散伙的问题,比如以后有本钱想单干了,这问题怎么处理?方强听了,脸色一阵红一阵白,急忙开口解释:
《重生1981:开局坟头挖宝!:杨一木林芳番外笔趣阁》精彩片段
杨一木又直接点明了散伙的问题,比如以后有本钱想单干了,这问题怎么处理?
方强听了,脸色一阵红一阵白,急忙开口解释:
西郊曾是洪泛区,如今荒草丛生。
一路倒是寂静,只有偶尔掠过的风,引得路旁杨树叶沙沙作响。
杨一木顾不得去欣赏野景,喘着粗气,一路疾走,一个多小时后终于到了坟场。
坟场的大门敞开着,门口长着两棵高大的落叶松,他紧裹了下衣服,目光警惕地向四周扫了一下,径直往里走。
先向东......再向北......无名坟?!
应该是它。
他兴奋起来,眼前这座坟茅草长得很高,虽是泥土坟,下面却是有砖块围的,估计以前也是家境不错人家,只不过后代没了。
坟洞在哪边呢?
总不能挖人家坟吧?
杨一木围着坟转了两圈,突然注意到西侧有几块砖上有一些泥巴,而旁边的砖上都生着厚厚的青苔。
于是连忙弓下腰,没一会儿就抠下一块砖。
哈哈,果然是这儿。
小样儿,挺聪明啊,竟然用泥把砖洞抹上了!
这会儿,他倒是不急了,取出黄纸,划了根火柴,点燃了,祭拜一番。然后又左右看了看,除了风吹过的“沙沙”音,鬼影都没有一个。
半蹲着身子,手伸进了砖洞......
空的?
砖洞里空空如也,什么都没有!
杨一木有些慌,跪在了地上,再用力往里伸,半条胳膊进去了,还是没有。
难道这是什么平行世界?有些人和事不一样?
还是朱大黑子说的假话?
瞬间,额头就出了一层细汗,后背一阵阵发凉。
一口吐沫更得是一个钉,说一个星期还上,就不能食言!如果此行没有收获,那......那真要带林芳往南去?
“如来佛祖、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......这些粮票来路不正,可一直藏在这里的话,未来就是一堆废纸!我只想救我姐,只想家人过的好一些......千万别让我白跑一趟,有朝一日一定回馈社会。”他心里默念着,用力地将又扯下两块砖,将整条胳膊都卡了进去。
摸到了,有东西!
杨一木心脏狂跳,欣喜若狂,拼命用力往里伸,肩膀卡在砖洞口钻心的疼。
两根手指终于扯住了一角,用力往外扯,卡的有些紧,再用力一扯......
终于将东西扯动了!
他将另一只手也伸了进去,将东西从砖洞里慢慢拖了出来。
这是一个用油毡纸包裹的小包,不到半尺长,约有成人胳膊粗。
抱着厚实的包裹,他就差亲一口,只笑道:“朱大黑子呀朱大黑子,兄弟我谢谢你了!”
用力撕开一角,露出一抹诱人的紫色,他嘿嘿一笑,伸手掏出了两沓。
这是一九六六版的全国粮票,紫色票面,约五成新,面值是五市斤,厚厚一沓用橡皮筋箍着,看样子至少有上百张。
有些遗憾!
如果是五五版的,再过三四十年,一张起码能卖一二百块钱!
不过现在也是硬通货。如果记忆不出错的话,这会儿一市斤全国粮票能换两角二,这么一小沓就能换一百多块。
再看另外一沓是一九七八年的姜苏省粮票,黄色票面,面值是二市斤,成色还挺新。
不用再看了,就是它!
发了!
此地不宜久留。
杨一木重新封好砖头,掏出袋里子的旅行包,撕开油毡纸,将一沓沓粮票都倒进了包里。
本想恶作剧一下,再将自己带的空袋子包进油毡纸再塞回去,想想朱大黑子那副复杂的小表情,心想还是算了,别在这货伤口上撒盐了,就着黄纸余火,一起烧了。
粮票大小类似一分钱纸币,所以哪怕两万斤粮票,因为面值的关系,旅行包也没装满。杨一木脱下外套,塞了进去,覆在上面。
拉好拉链,拍了拍裤子的土,将腕子上的泥土搓净,拎起来就往坟场外走。
坟场大门外,夕阳西斜,野风劲吹,卷起了地上的尘土和枯叶,在空中打着旋儿。
杨一木径直往大路上走,忽然发现林场那边走过来一个人,拐上来和他迎面而行。
待会面时,那人望了他一眼,问道:“哎,干什么的?”
杨一木弓腰低眉,沙哑着嗓子,尽量让声音悲伤一些,说道:“给长辈来上坟。”
“上坟?”那人狐疑地重复了一遍。
“是的。”杨一木说。
“清明早过了,现在来上坟?”那人一边上下打量着他,一边问道。
杨一木从裤兜儿里掏出一包烟,抽出一支,一边递过去,一边说道:“这不是家里老人病了吗,算命先生说这是过世的亲戚在下面念叨了,得过来烧些纸拜拜......”
“哦哦。”那人接过烟,点起来,说道:“要的,要的,烧点纸就好了。”
“行,老哥,那我先走了,还得赶回去。”杨一木说着转头就走。
那人在后面又叮嘱了一句:“小伙子,柴滩荒,步子快些,天黑了,蛇也出来了。”
“好好好,谢谢,谢谢!”
那人慢悠悠的走远了,杨一木嘿嘿一笑,多亏自己机灵。
虽说他们只抓进林场偷木材的,可如果发现这些粮票,绝对得把自己按在这儿!
那人倒是说的不错,柴滩地进来容易出来难。
杨一木摔了两个踉跄,一路急赶慢赶,天黑的时候,终于走到了县城边。
找了个公厕,八个蹲坑一个人没有,他进去以后,解开裤子撒尿,热气腾腾,低头看了一眼,尿都黄了......
出来后,乐呵呵地套上外套,拎着旅行包,正准备找家旅舍住下。
一摸口袋,靠,钱不知道什么没了,也不知落在坟场,还是掉在路上。
杨一木咧嘴一笑:“算了,破财免灾吧!”
也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。
当晚,杨一木编了个小偷的故事,花了两市斤粮票,找了家旅舍住下,还蹭了老板娘一顿晚饭。
吃过晚饭,他将门一关,拉开包将粮票过了数:全国票五市斤的一千张,二市斤的八百张,一市斤的一千二百张,五两的二千张;苏省票五市斤的一千张,二市斤的一千二百张,一市斤的八百张,五两的二千张。
全国票比省票值钱,省票只能在省内用,如果出省办事或者探亲,就要粮食所兑换全国粮。
不够用怎么办?
只能去黑市买。
杨一木虽然不知道老家这边现在什么价格,不过保守按一毛九算,光是拿到黑市上卖,二万斤就是三千八块,还上刁青松那笔钱,还能剩下一千块!
大概鸡叫三遍的时候,杨一木便起了床。
他随手扯了张旧报纸,包了几沓粮票,用袋子裹好揣进怀里,准备进城。
出门的时候,又特意叮嘱老板娘,这几天他会一直住在这里,房间不用打扫,等晚上回来再一起结账。
这家旅社位于城郊结合部,属于“三不管”扯皮地带,反倒比城里安全些。老家暂时不想回,来回也不便。虽然这两年开放多了,但是做生意还是要小心,何况他这种生意......搞不好得挨枪子。
进了城,杨一木直奔城南菜场,那里有一个自发形成的地下粮票交易市场,又称“粮票黑市”。
到了那里,天色尚未大亮,朦胧的光线将周围的矮屋景物映得影影绰绰。
早到的小贩已经摆好了摊,叫卖声是肯定不会有的,毕竟这还是个“投机倒把打游击”的年代!
杨一木花了二斤粮票,在包子铺换了三两包子,匆匆吃完,又要了一杯开水喝了一点,就赶紧占好位置。
后世香港电影那句“如果那个人做事不专心,又看着你的话,他就是警察!”
如果换到杨一木的身上,那就是“如果那个人摊子前啥也没有,又看着你的话,他就是粮票贩子。”
这年头,粮票是硬通货,没有它,出门寸步难行。要是赶上红白喜事,还得去粮管所申请“周转粮证”,借粮食应急。
可借了粮食,怎么还呢?
总不能日子不过了,全家喝西北风去。于是,黑市成了唯一的出路。
天慢慢地放亮,路上的行人渐渐多了,买菜的人也多了。
他转了一圈,看到不远处有个小伙子老神在在蹲在那儿,一声不吭,光是抽烟,看样子像是同行。
走过去一问,果然如此,又问了下价格,心里有了底。
“大姐,您是出差还是办事?我这儿有全国票和省票。”好不容易看到一位大姐在他摊前驻足不走,现在不卖瓜,要等到什么时候。
“什么价?”大姐问。
“全国票二毛三,省票一毛八。”杨一木笑着回道。
“这也太贵了!我家里头五一给儿子办喜事,要得多,一毛六行不行?行的话,给我200斤。”大姐讨价还价。
杨一木心里叹了一口气,什么时候他都做起了二分钱的算计,越想越没劲。
上辈子自己回老家后,先在乡中教课,教了一年,据说误了不少弟子,被发配到校办厂,半死不活拿份工资。
校办厂主要生产粉笔套这类小玩意儿,用废纸卷成的圆筒,套在粉笔上,防止粉笔灰弄脏老师的手。
整天和一堆老娘们打交道,杨一木满心失落,整天无精打采。
生活还得继续,浑浑噩噩一直混到一九八七年。
那年他弟杨二力相了门亲,家里原指望他给出把力,可他连一千钱都拿不出,最后全靠老娘觍着脸四处求人。
为这个,二力一直抱怨他这个做大哥的不帮衬弟弟。
杨一木苦恼了好一阵子,后来才想明白了。
这年头端公家饭碗的瞧不起小商小贩,实不知此时不过都在囚笼里跳舞而已,自己那点工资根本不靠谱,别说家里就连他自己也指望不上。
用后世的眼光再回头看,没啥意思,死熬死守着这份旱涝保收的工作,却错过了这个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年代。不甩掉铁饭碗这个包袱,根本不可能赚更多的钱。
直至那时,他才大彻大悟,发誓不再胡混。
先是办了停薪辞职,找校长承包了校办厂,改做起了包装生意,接着涉足食品加工,将产品卖到了棒子国、矮子国。
一九九二年,他开始涉足供应链管理,生意越做越大,后来进入餐饮行业,凭借独特的菜品和优质的服务,将分店开到了省城和沪市。新千年后,他试水连锁经营领域,不久就形成了覆盖多个城市的餐饮网络。
想不到一场非典,击垮了他所有的梦想。苦苦维持了几年,还没翻身,又是一场金融危机,他的资金链断了,终于撑不住了。
想他一生风光过,也落魄过......
“大姐,还没开张,赚个一两分的跑腿辛苦钱,真不赚你钱,就图个顺当。”
杨一木麻溜地数了200斤省票,用橡皮筋捆好,又额外拿了四张五两粮票递过去,说:“大姐,这是200斤省票,一共三十六块钱,我这多给你几张,就送你了。你要是有熟人出差办事,回头帮我介绍介绍。”
“你这小伙子生得文绉绉的,倒是个做生意的料,说话也中听。”大姐接过粮票,数了数,满意地付了钱,转身离开。
第一单生意成交了,杨一木绷着的神经也松了下来。
后面的买家大部分零碎过来的,几分几毛、鸡零狗碎的没什么劲,人家多要了一张两张,杨一木也不跟人家计较,大大方方就给了。
做生意嘛,都是上赶子的。
这边人一多,那边原本在谈生意的人也凑了过来,哪怕让个一分二分,也装作没听见,直奔杨一木这边。
偶尔会围过来几个农民模样的,提着鸡蛋或者自己抓的河蚌、鱼虾要来换,都是鲜活的。
农民是没有粮票的,按照参加集体劳动的工分,可以分得口粮。
改开后,安州这地界农村经历了联产到组,包产到户,一九八三年才实行大包干,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,真正的包干到户。
眼下,富平这边还处于联产到组和包产到户的过渡期,一季麦子,一季稻,两稀一干搭点红薯干,粮食勉强够吃,但孩子多、壮劳力少的家庭粮食就不够吃的,还得另外想办法。
有些聪明又胆子大些的就拿着家里舍不得吃的鸡蛋或者自捕的鱼虾,跟城里人换吃不完的粮票,再用粮票加钱去买细粮拿回农村改善生活。
日上三竿时,杨一木手里的两千斤粮票还剩不少。
但他不敢卖了,像在富平这种小县城倒卖二十四类并不多见,但倒卖粮票就在抓与不抓,毕竟还没有法律明确这种行为是否合法。
何况,他的粮票数量这么大,又是来路不正,从坟洞里扒出来的。
别给打草搂了兔子!
他也不敢在大街上明目张胆,细数卖了多少钱,匆匆收拾好东西,赶紧往回赶。
走到半道,又热又渴,找了个没人的树荫下坐着,从怀里取出钱袋,掏出一大把钞票,还有粮票。等一张张理好,又过了个大数,粮票还剩不到八百斤,手里多了二百二十九块三毛。
才二百三不到?
杨一木心里不免有些捉急!
满满当当装了三架车,杨一木、方强和竹竿先送一趟,船师傅守船。
三人一路走一路歇,到了水产公司,已经人来人往,都急吼吼地往早市送货。
几人一合计,竹竿留下负责看货,杨一木和方强返回再拖一趟。
最后,船师傅也拖了一车,不过有些不情不愿:“这钱可不在那四十块钱里,得另算啊?”
等货物码好在秤站旁边,杨一木让方强和竹竿在原地等着,自己径直往办公楼走。
还没走两步,他感觉肩膀被人从后面按住了,回头一看,正是昨天遇到的那位老头。
杨一木立刻掏出烟,笑着打招呼道:“大爷,早啊,来支烟。赵经理来了吗?”
老头把烟夹在耳朵上,摆摆手说道:“这才什么天啊,赵经理没那么早来。不过他昨天已经在我这儿交代好了,你直接跟我过来就行。”
说完,老头便带着杨一木往秤站走去。
到了秤站,杨一木赶紧冲方强他们招手,示意他们开始卸货。
秤站里有一排排水槽,靠外口的是鱼池,里面养着的都是安州本地的淡水鱼,像草鱼、青混、花链、青鱼这些,里间则是一排空着的大池子。
杨一木打开袋口,伸到老头跟前,说:“大爷,你瞅瞅这小龙虾敖大肉肥,个个都是顶好的。”
老头瞥了一眼,没多说什么,冲着旁边的人喊道:“把地磅推过来,赶紧上秤!”
称完重,老头让人把里面死了的、小的挑出来,又扣了二十斤水分。最后一算下来,一共比他们在家称的重量少了八十六斤。
杨一木也没多计较,沿着秤站走了一圈,一边挨个给每人都递了支烟,一边用仰慕的眼神和钦佩的语气喊着“大哥大姐”,态度恭敬得几乎要喊“亲爹”了。
方强他们帮忙站里工人把小龙虾和大鱼倒进池子里,杨一木则拿着收据单,欢天喜地地跟着老头去后面小楼的财务室结账。
结完账出来,杨一木笑着对老头说:“大爷,您真是帮了大忙!”
接着,他指了指方强他们,介绍说:“这两个是我兄弟,那边年长些的是我们村的机船师傅。以后还得请大爷费心,多帮衬着点。”
拿到钱,杨一木心里轻松了不少。
赶了一夜的路,又干了这么些活,肚子都饿了,便叫上方强他们一起在水产公司门口吃早饭。
门口有卖包子、豆汁的,有卖煎饼果子的,杨一木花了两块二毛钱要了四斤肉包子和五碗豆汁。
也不得不说,这年代钱真的很值钱,购买力强悍,一斤包子五毛,一碗豆汁才要二分钱。
几人围坐在桌边,看见大肉包子早就两眼放光了。
吃饱喝足,就往回走,一路上方强一直紧紧跟着杨一木,生怕杨一木一不小心口袋松了。
上了船,杨一木和方强各自掏出一大把钞票,堆在一起,一张张认真地摊开码齐,过了个大数。最后一拉帐,把收鱼虾的成本去掉,尽赚四百九十块五毛五。
这可把方强吓坏了,忙问:“哥,你没算错吧?”
杨一木笑了笑,手一推说道:“你来。”
方强接了过去,又连着数三遍,渐渐地小眼睛开始眯了起来,显得眼睛更小,最后一拍手,连声嚷道:“哥,哥,我们发了。”
哎哟妈呀,就这两天不到时间挣了这么多好钱,真是开眼了,他能不激动吗?
杨一木没理他,笑着给竹竿和船师傅分了钱,
竹竿一天十块,给了二十块钱,一三也按标准,给了二十,不过人不在,要等到回去给。
船师傅工钱事先讲好的给四十块,杨一木多给了一块,又塞了一包烟,算是拖了一趟货工钱。
船师傅姓夏,嘴早笑歪了,一天四十块呢,都赶上城里人一月工资了,这还是往高里说的,一般上班的也就一月二三十块钱,四十往上那是高工资了。
此时,心里也就盘算开了:柴油是生产队的,自己就出个力气,白得四十块,一个月一千二,一年就是万元户?
做梦的吧?
一捏大腿,疼啊!态度上却对杨一木热情了不少,多给的一块也坚决不肯要,怕因小失大,黄了事情。
杨一木也没坚决,一块两块的事儿推来推去没啥意思,还是那话友情后补。
竹竿也推辞不要,杨一木倒是认真了,说道:“拿着,都是一样兄弟,没有道理我们挣钱,让你白忙活的道理。再说,后面你和一三还要继续帮衬着我,又不是干一天两天的。只要这事干一天,你和一三一天拿十块。”
按照现在的行情,给个二三块也就顶天了。
可不是有老话吗,不患寡就怕患不均。
杨一木也没有矫情到去和一三、竹竿他们搞合伙或者分成,眼下他缺钱,欠刁青松那笔款子,他心里有点着急上火。
加上今天分的,口袋里一共才八百块,如果到时间还不够,拉上方强再出一部分粮票,先把林芳那事儿给解决了。
竹竿可就高兴坏了,他也是去年返城的,一直没安置工作,他爸觍着老脸,四处求人,就连安排个街道厂工作都在等通知之中,等了一年了,还在研究呢。
其实他心里也清楚,街道厂效益不好,基本没啥福利,半死不活,一年顶死也就一二百块钱。心里又算了一笔帐,如果真按杨一木说的,一天十块,那一个月就是三百块,这个搁在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儿。
干一天活,就拿一天钱,合情合理。现在杨一木给他这么多钱,纯粹就是照顾自己了。
不要说十块钱,就是给个五块钱,在大街上吼一嗓子,估计能从城南排到城西。他爸在车辆厂六级工,一个才拿四十六五,算起来比他这活差太远了。
这活除了熬人熬夜,不要太轻松好吧。
竹竿心里想着,到家后抽空回去一趟跟他爸商量下,不要低三下四求人了,街道厂那工作谁爱干谁干,他是不伺候了。
到了家,船靠岸,已经十一点多。
进了门,院子里正吵吵嚷嚷,一三和方兵忙着收货过秤,忙得眼都不抬。
杨一木过去瞅了一圈,十几口大缸早已满满当当,红通通一片。
方强老娘正在灶屋里忙饭,一听方强这趟就挣了一百六十二块钱,一边高兴一边担心,毕竟这是投机倒把的事,低声问道:“强啊,这不会真的出事吧?”
方强老娘平常一分钱都恨不得掰成两半花的主,如今见到如此钱景,突然有了盼头,连忙拿了一块钱让小儿子方兵去街上割肉。
等方兵拿肉回来,切了一半,想想又将搁到碗柜里的另一半又放到了案板上。
方强返城这两年,大儿子方军媳妇吵吵闹闹吵着要分家单过,话里话外意思嫌二叔子没工作,小叔在上学拖累他们,总不能拿自己两口子工资钱补他们吧?为了这事,老两口也没少唉声叹气。
杨一木跟着忙了一阵,院子里人少了,终于清净了下来。
方强老娘出来,招呼大家上桌吃饭。
今天入夏快,气温格外热,杨一木身上汗津津的。他借着方强的毛巾,在小河码头上捞了一把脸,终于感到凉爽了些。
进了堂屋,一盆油亮亮的大肥肉放在八仙桌正中。
一番谦让后,人还没坐定,方兵已伸出筷子往肉盆去,却被他老娘一巴掌打了回来:“一点规矩都没有,你杨哥还没动筷子呢。”
方兵嘻笑一声,半大小子,正是长身体的时候。杨一木忙抓过筷子,夹了两块大肥肉放进他的碗里。
方强老娘拎了小儿子胳膊一下,佯装生气道:“你这小东西,一点不知道当家油盐贵。你咋买的五花肉?啊,根本一点油水都没有。”
她有点心疼呢。
这年头,一般人家买肉都喜欢膘大肉肥的,炸了油,还能炼出油渣烧菜。
香喷喷的大米饭,加上一盆子红烧肉烧土豆,一桌子人吃得油光满面,连盆底都被刮干净了。
杨一木却心酸得不得了,刚才那一幕,让他想起了五十里外的老娘和弟妹。
他老娘叫张兰英,是富平县郑庄公社杨家河村的一个普通农民,今年刚四十。
这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女人,性格说好听点叫要强,说难听点叫“头硬”,“头很硬”——该认的事,打掉牙和血咽,多难都认。
这本不是一个描写软弱女人的词,可偏偏又只能这样形容,反正在她的人生词典里,嫁鸡随鸡、嫁狗随狗是她人生至高无上的目标。
一生操劳,可悲居多。
杨一木是家里的长子,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后第一次高考,考上了安州师范学校,也就是后来的安州师范大学,成了杨家河村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。
杨一木下面有三个弟妹。
大弟杨二力,今年十八岁,只上到了初中毕业,在家务农。上辈子他媳妇为了结婚借的那一千块钱,闹得全家鸡飞狗跳,一地鸡毛。
与方强大哥那媳妇有得一比,也是坚持要求分家单过,自己长得五大三粗的弟弟硬是被她拿捏得死死的,又因为养了个丫头,被老娘埋怨了无数回,一辈子窝囊得要死。
妹妹杨三妹是家里唯一的女孩,今年十六岁,还有三个月要参加中考,成绩还不错。上辈子她是考上了县一中的,可录取通知书被老娘藏了起来,那个破败不堪的家供不起她继续学业,所以她和农村多数女孩一样,接受命运安排,回家当了农民。二十岁早早嫁了人,幸运的是妹夫对她不错,也减轻了他不少的愧疚感。
幺弟杨八同,今年七岁,名字是由麻将桌上八筒演变而来,却是他家最有出息,也是过得最幸福的孩子。前世他考上了南大,进了省报,找了一个教师老婆,家世不高,但丈人一家把他当儿子待,婚姻也很美满,一生过得相当幸福。
一家人,杨一木最不愿提起的就是他爸。
他爸叫杨胜利,是公社时代八大员之一的“放映员”,没有编制,拿多少工资,家里谁也不知道,他也从没有拿回来过。一到青黄不接的时候,就往外跑,他有一个姐姐也就是杨一木的姑姑嫁在鞍山。
这个时候,不知道杨胜利流浪到哪里去了,反正杨一木重生后就没见到他。
就这么一个只顾自己吃饱全家不饿的人,就这么一个连子女名字都懒得起好的人,在生产队的时代自然落不了好名声。
家里人多,但是壮劳力工分一个没有,张兰英一人带着四个孩子,前些年长年都是野菜黄薯干,这些年日子强了些,但也就是采子米加黄薯干,除了大弟杨二力出奇地长成了五大三粗的大汉,其他孩子一个个吃得面黄肌瘦。
不管前世还是现在,他一想到这些,都心酸得想哭。
他想回家看看,看看老娘,上辈子有段时间他恨她心狠。一直到她临死,他才醒悟,他是家的希望,他根本没有资格为了爱情而任性。
可现在老娘还在气头上,自己干的又是投机倒把的事情,粮票又来路不正,万一......
他不想牵连家里人!
吃完饭,哥几个继续招呼送鱼虾过来的。
杨一木不禁感叹年轻就是好,能折腾,来回赶了十几个小时,还能撑得住。
可到底是年轻啊,又都是小伙子,一遇到大姑娘、小媳妇两分三分的,根本不好意思跟人家张口计较。
这可把在灶屋里忙着的方强老娘心疼坏了,哪能这么做生意,这些骚婆娘,全占人家便宜,呸,锅碗也不收拾了,抹了下手,出来就招呼:
“哎呀,你们这些小年轻啊,哪能连轴转,别熬坏了身体,你们不疼,娘老子还疼呢。留一人在这儿,今个下午不上班,有我在这儿帮着就行了,又不是什么体力活,其他人都轮流去睡一会儿。”
她这一说,杨一木顿觉困意席卷,眼皮子打架,也没强撑着。一三不赶夜,让他在这儿顶一会儿,就和方强他们溜进屋去午睡了。
方强老娘也是能干人,收鱼虾,称秤,算账,结款,一点也不比年轻人差,干得非常起劲。
院子里不停地吵吵嚷嚷,咳嗽声,赶路声,论价声,声声不息。
杨一木倒睡得安稳,一觉醒来已是下午四点。出门一看,院子里又站了几个人,都是提着口袋过来送鱼虾的。
方老头下班早,也在旁边帮着他们上秤,他妈和一三用布头在扎袋口。
杨一木想着两天没去旅社,账前面付清了,可东西放在那边,实在不放心,又回了趟旅社。
回来的时候,天刚黑下来。
院子里刚走了一波,方强老娘招呼大家赶紧进屋吃饭。
晚饭依然吃的干饭,一碗蒸蛋,一碗茨菇烧肉,一盆青菜汤,可把方兵高兴坏了,顿顿有肉,还上了蒸蛋,这小日子过得不赖,嘿嘿嘿......
方老头开了一瓶白酒,给杨一木、方强和竹竿面前一人倒了一杯。
杨一木推说不喝,方老头说:“年轻小伙子,哪能不喝酒?”但看见杨一木真的没碰,他也就没坚持让喝!
前世二零零三年那场疫情以后,杨一木靠着积累勉强咬牙挺过,可都是怕了,生意越来越惨淡,家里经济来源越来越少,到了二零零八年他彻底扛不住了。
生意没了、公司倒闭不说,还欠下银行六百多万,原材料供应商货款四百多万,以及亲戚朋友二百多万。
都说夫妻是同林的鸟,大难来了各自飞,果然老婆天天和他吵架。
为了避免后续起诉,房子被人收走,一家人流落街头。
杨一木选择和老婆离婚,房子、车子和手里仅有的一点钱全给了她和两个女儿。
当初商量好了,等事情了结,等把亲戚朋友私人借的钱还上,他们再复婚。
自己当回恶人,最起码妻女能有依靠,可仅仅过了不到三个月,她就结婚了,新郎是个矮胖子......
接连的打击,让他的人生进入了至暗时刻,可一切太迟了。
他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了,还被那坏婆娘摆了一道,演了一场大戏,竟然没发现......
后来他堕落了,或者说连死的心都有了,天天酗酒买醉,以至现在都想不起来,到底是哪一次买醉让他又重生过来了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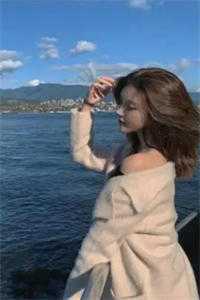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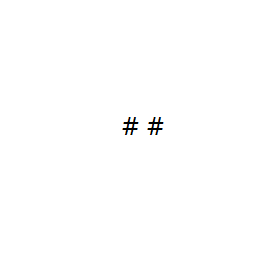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